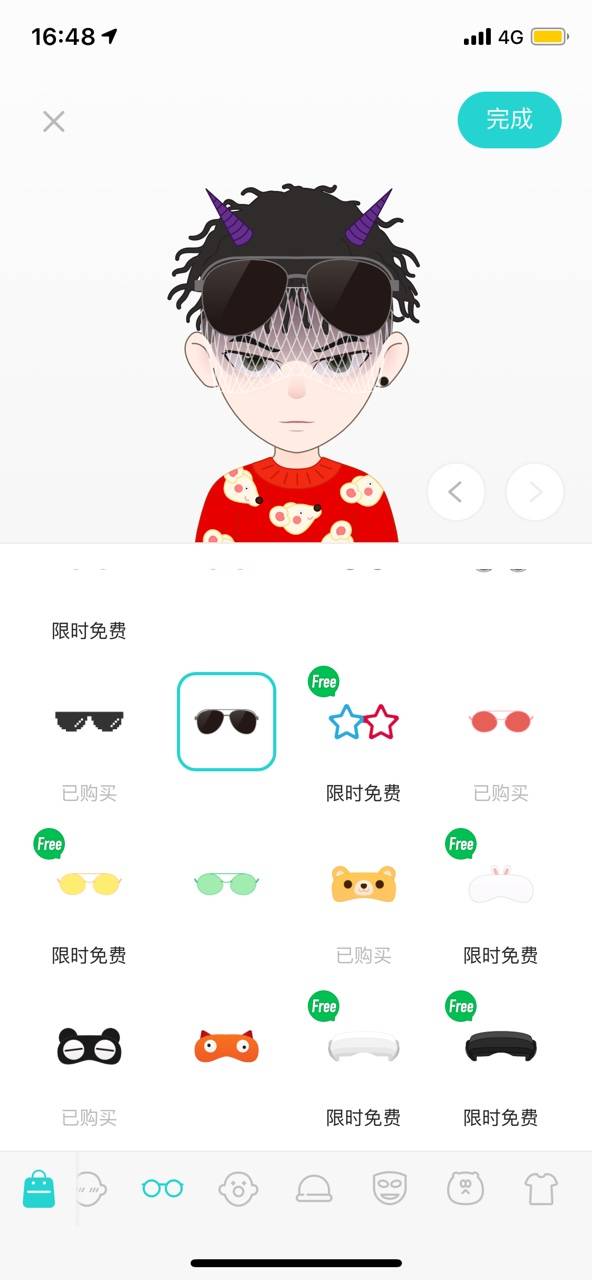国家文物局9月28日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通报了包括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在内的四处遗址最新考古成果。

28日,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探方的灰坑中。出土简牍目前仅清理了一小部分,发现字迹明显的简牍残片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1000余片,已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是反映西汉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据了解,考古人员2021年至2022年在晋宁河泊所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500多枚封泥。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西汉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汉代时期滇池水面还没今天宽阔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位于滇池东南岸,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一直被当作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为厘清石寨山墓地与周边各遗址的相互关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4年开始对滇池东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分片区逐年进行考古普探、重点勘探,发现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具有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遗址核心区面积为4平方千米。在考古调查、勘探的同时,建立了滇池东南岸和滇池南岸的测控网和考古数字平台。在勘探的基础上,先后对西王庙(2016年)、上西河(2017年)、河泊所村东(2018年)、上蒜一小北侧(2021年)等7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发现了早于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和汉置益州郡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
河泊所遗址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发掘以来,特别是1956年6号墓出土“滇王之印”以来,乃至整个20世纪,云南省青铜时代考古主要围绕墓葬进行,在聚落遗址方面着力不多。1990年,为配合昆玉铁路建设而进行的玉溪刺桐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首个爆发点。刺桐关遗址的发掘,首先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以同心圆纹红陶盘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错误认识,在该遗址的堆积中发现这些红陶盘和青铜小件工具乃至汉代陶器共存。
2006年,在昆明西山天子庙遗址首次发现了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尽管遗迹现象不多,但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与在墓葬中出土的同样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了近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并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2016年至2017年,在西王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汉代和早于汉代的滇文化时期乃至时代更早的先滇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存。有意思的是,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的滇池水面要低3至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反过来说,那个时期的滇池还没有现在的滇池水面宽。西王庙遗址的发掘,标志着在石寨山—河泊所遗址考古中聚落遗址的发现取得重大突破。
曾出土“滇国相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靠每年国家局批的发掘项目,同时开展发掘、勘探和整理工作。每年安排一平方千米的考古勘探,安排一到两个小项目的整理。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对河泊所村东的地块进行了发掘,揭露出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如此众多的瓮棺,在国内也不多见,在滇文化分布区内也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葬俗”的认识。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资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这也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2018年的考古勘探中,发现在河泊所遗址的南部地区,存在着一条自西向东的埂子,含沙量相当大。为了弄清楚该沙埂的形制、构造和功能等诸多问题,2019年7月至10月,对河泊所村西南角的沙埂进行了发掘,之后又在东端、位于金砂村西北角的沙埂另一端选点发掘。发掘表明两地沙埂的内部结构、堆积方式是一样的。
2020年9月至12月对河泊所村和下西河村之间、西王庙以北、南邻金砂路的范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堆积厚度深1.45~5.8米,包含了西汉中期以前、西汉至东汉以及明清时期的堆积,以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堆积最为丰富,共发现遗迹330个,出土文化遗物320余件。根据现场湿筛、浮选和鉴定,动物骨骼至少包括了牛、猪、羊、鹿及丰富的鱼类和螺蛳,植物遗存至少包括小麦、稻等农作物。这些遗存可初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遗迹是成排的火葬墓和一个散乱堆放人骨的人骨堆,以及一批竖穴土坑墓;中期阶段是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和遗存较为丰富的阶段。墓葬和人骨堆的发现是汉代文化堆积中发现的另外一类重要遗迹现象,共发现有14座墓葬,这些墓葬分布相对集中,葬式奇特,包含了双人侧身屈肢葬、单人侧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仰身屈肢葬等;早期阶段最重要的发现是位于台地6边缘的河道9,并弄清楚了台地6与河道9的关系。
通过上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初步确认了滇文化的核心区域——河泊所遗址群的大致分布范围,即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以西及滇池以东的区域。其核心分布区约4平方千米。
发现字迹明显的简牍残片200余片
2021年3月至12月,对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一小北的区域(台地38)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区堆积厚度1.9~3.6米,除洪积层堆积外的文化层堆积厚度为0.4~2.5米。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阶段的堆积最厚,遗存较为丰富,发现了大型道路和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烬堆积、房址、水井、墓葬等遗迹441个。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类编号文物300余件,有铜器、铁器和各类生活用陶器、玉石器、骨蚌器等。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包括筒瓦、板瓦、瓦当、菱形纹砖等,绳纹瓦的数量可占到80%左右,筒瓦长度可达48厘米。带榫卯结构的方形砖可能为铺地砖,表明建筑的等级规格较高。
一个重要发现是封泥。发掘区北部边缘为一条古河道,河道内出土大量遗物,约占总量的1/3,其中封泥就是典型的代表。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封泥集中出土于灰烬堆中,推测为灰烬堆或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灰烬堆中发现的条状炭化木条,更进一步证实了此猜测。出土的一批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两种。根据河道废弃堆积内的出土物,判断其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简牍。2022年的发掘区在2021年发掘区的东、北区域扩展发掘450平方米,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探方的灰坑中。出土简牍目前仅清理了一小部分,发现字迹明显的简牍残片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1000余片,已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郡,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辖24县。《汉书·地理志》有:“益州郡县二十四:滇池、双柏、同劳、铜濑、连然、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味、昆泽、叶榆、律高、不韦、云南、嶲唐、弄栋、比苏、贲古、毋棳、胜休、建伶、来唯。”
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2021年至2022年发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益州郡和所辖属县的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达18个。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权的有力证据。从西汉中期武帝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了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突破,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
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发掘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48厘米的瓦片、瓦当和铺地砖等,表明西汉设置的益州郡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
滇“置吏入朝”之后,古滇国既有滇王“复长其民”,又隶属于益州郡管辖,结合以往工作中出土的滇王金印及“滇国相印”封泥,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滇王”治理和郡守长官治理两套体系均有了实物证据,让石寨山大遗址考古也取得了重大的新的突破。